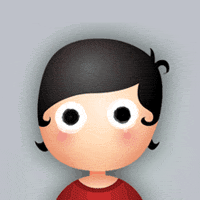白蕉:云间谈艺录
临池剩墨
《临池剩墨》整篇有一千八百余字
通篇都是谈论自己对书法的心得体会
作书力在内者王,力在外者霸。若过于鼓努为力,肆为雄强,则张脉贲兴,将如泼妇骂街,成何书道!
柳深于《十三行》,米深于《枯树赋》,消息似可见。
藏锋所以蓄气,用笔欲浑欲遒。其实藏锋便是中锋,《九势》所谓令笔心常在笔画中行者是也。后人所谓锥画沙、折钗股、如拆壁、屋漏痕,端若引绳者,故是一理。惟浑而能遒,则精神出矣。
孙虔礼云:“察之者尚精,拟之者贵似。”此故是临习初步。盖临书,始欲像,终要不像;始要无我,终要有我;始欲能取,终要能舍!唐人无不学右军,宋人无不学鲁公,及其成也,各具面目。鲁公师河南,然鲁公绝非河南。正在其能翻一局,所谓智过其师,方名得髓也!东坡称书至于颜鲁公,正善其妙能变化。若钱南园之学颜,则正是僧皎然所谓钝贼者也。
或以偏锋解作侧锋,非也。侧锋之力,仍在画中。因势取妍,所以避直而失力。玩钟王帖,可悟此理;旭素草书,亦时有一二。
有一字的布白,有字与字之间的布白,有整行乃至整幅的布白,此即古人小九宫大九宫取义所在,亦即隔壁取势之说。合整幅为布白者,三代金文中多见之,《散氏盘》为著,《十三行》则后来媲美。然此正所谓同自然之妙,初非有心为之。否则如归、方评史记,直使人死于笔下!
金文之不合全章为章法者,其行法绝精。晋人书牍,行法似疏实密,学者留意于此,可以悟入。今人书牍无可观者,于此等处正复少用心。
作书分间布白,行法章法,魏晋人最妙,宋人尚多置意,明以来鲜究心,此实有关气味者。
观《爨宝子》,正不必惊其结体之奇,当悟其重心所在。字有重心,则虽险不危!
作书用笔,方圆并参,无一路用方,一路用圆者。方多用顿笔、翻笔;圆多用提笔、转笔。正书方而不圆,则无萧散容逸之致;行草圆而不方,则无凝整雄强之神。此相互为用,似二实一,似相反而实相成者也。
用笔太露锋芒,则意不持重。不但意不持重,实是意尽势尽,则味亦尽矣!
唐以诗取士,故诗学蔚为一代文学特色;帝王能书者多,故书学亦特别发达。今人学书三年,动自命为书家,倘一观唐代不以书名者之尺牍,直宜愧死。
昔人有状王、张、颜、米诸家之书者云:“右军似龙,大令似蛟,张旭似蛇,鲁公似象,怀素似犀,南宫似虎,东坡似鹰,子昂似蝶,枝山似兔,香山似莺。”诚为妙思隽喻。
棋差一着,满盘皆输。似正说写兰,一笔不合,全纸皆废也。我意学王书亦正复如是。着一败笔,即觉从纸上跳出,直刺入眼。不似学六朝石工陶匠之字,三月便可欺人也。
邓完白篆刻自成一家,其书深于功力。篆书面目自具,虽古意不足,毕竟英雄能自树立;隶书入手太低,无一点汉人气息,比之钱梅溪略胜一筹而已。
包慎伯文章议论,远在其书法之上,然其好作玄论,故示神秘,最为可厌!其书中年由欧颜入手,转及苏董,志气已低。其后肆力北魏,晚年又专王。尝见其墨迹,小真书稍可观,草书用笔,一路翻滚,大是卖膏药好汉,表现花拳模样;康长素本是狂士,好作大言惊俗,其书颇似一根烂绳索。
云间随笔
原文有五千字左右,
四十章节。
该篇章主要是议论书法、写兰及评判古人之作。
故亦绍介二三于读者。
作书要笔笔分得清,笔笔合得浑。分得清,然后见天骨开张;合得浑,然后见气密神完。
于转换处见留笔,能留笔即知腕力。“抽刀断水水更流”,则所谓端若引绳者矣!舞剑斗蛇,莫非此理。
凡艺事初事学习,如食物然,先入口,能受也。及沉浸其中,酊酩有味,则入胃肠,贵能消化也。能消化谓吸取物之精华,为我身之益。我未见多食猪肉而成猪腔,亦未见多食牛肉而成牛精也!
延五年,吴郡沈右为彦清题怀素《鱼肉帖》云:“怀素书所以妙者,虽率意颠逸,千变万化,终不离魏晋法度故也。后作草皆随俗缴绕,不合古法,不识者以为奇,不满识者一笑!”此是见道之言。东坡题王逸少帖诗云:“颠张醉素两秃翁,追逐世好称书工,何曾梦见王与钟,妄自粉饰欺盲聋,有如市倡抹青红,妖歌曼舞眩儿童。谢家夫人谈丰客,萧然自有林下风,天门荡荡惊跳龙,出林飞鸟一扫空。为君草书续其终,待我他日不匆匆。”嬉笑怒骂,故是当行快语!学者于龙、空、匆三韵,宜深体味。今世人作草,个个芦茅草团,如言满眼藤蔓,或春蚓秋蛇,尚觉非是耳。
执高腕灵,掌虚指活,笔有轻重,力无不均。
学章草由篆隶沙简入,学散草由楷行入。此两途,未可别立异说也。然学钟王楷行,自欧虞入,故是一路。而中间过程,帖与《圣教序》,则必须致力者要在终能换去面目。否则学之者多,见之过稔,便贻讥俗书耳。
草书不从晋人入,终无是处。
草书大别为章草、散草、连绵草三种。而章草实为我国早期之简体字。晋人草书书法,字多个别,而气脉贯注。其字迹相连者,不过二三字,所谓散草也。前人因欲别于章草,亦称今草。旭素而后,盛行连绵草,而草法遂坏。世誉草书之美,每曰“铁画银钩”,余谓此四字正见匠气,非所以知晋人草法,差是形容其熟练有骨力耳。
余于书不薄颜柳,而心实不喜。论其楷则以颜有俗气,柳有匠气。米南宫云:“颜柳挑踢,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,从此古法荡然无遗矣!”实非过语。然颜柳书佳者,如《三表》、《争座位》、《祭侄稿》、《鲍明远》、《马病》、《鹿脯帖》,实襄阳所师。余尝谓颜书正楷大字,除雍容、阔大、严肃,有廊庙气象而外,别无好处。《多宝塔》为举子干禄所法,原属梁隋人一路写经体。行书如《三表》诸帖,其甜使人爱,实亦容易误人。至何子贞书《金陵十二咏诗》,必圈令如《争座帖》、《祭侄稿》,亦可哂矣。
余早岁临池,夙以之自负。遇得意,自钤“晋唐以后无此作”印,狂态可掬。然迄今未敢以此席让人。
摹得形质,临在形质与情性,看、背则情性兼形质。
凡为艺,一矜持便是过。矜持虽非做作之谓,然已不复见真精神流露矣!我非不喜穿新衣服,但穿之身上,处处令我不便,因有惜物之心存也。必如宋元君解衣盘礴,庖丁不见全牛乃可。若名笔在手,佳纸当前,略存谨慎,便尔矜持,遂损天机矣!
黄鲁直云:“书欲拙多于巧。近世少年作字,如新妇之妆梳。百种点缀,终无烈妇态也!”余谓近世书人,亦多巧匠。作篆隶无一笔入古,正坐此病。学帖尤忌如新妇妆梳。赵董二文敏作书,欲直接晋人,其心何尝不雄,其行楷何尝不词不美。但赵固似娼妓,董亦无烈妇态。固知其品性不同,而就而言,亦缺深沉也。
书学上有碑帖之分。然世俗初学,必由碑入,此于理正自暗合,转而入帖,乃见成功。我尝谓在历史上言,帖为碑之进步;在学书上言,碑是帖之根基。未可如安吴、南海一辈,有奴主之见,好奇之谈。若言碑帖大别,有可得而言者;碑沉着端厚,重点画,气象宏肆;帖稳秀清洁,观使转,气象萧散不群也。萧散二字,最好解释,正是袒腹东床,别于诸子矜持。
学帖大弊,在务为侧媚。侧媚成习,所以书道式微也。我国书法,衰于董赵,坏于馆阁,所谓忸怩局促,无地自容。陆梦云云:“处女为人作媒,能不语止羞涩。”此所以戒学者取法赵董为下也。项穆言:“书有三戒:初学分布,戒不均与欹;继知规矩,戒不活与滞;终能纯熟,戒狂怪。”数语甚简要。科举功名,影响于书道,病在太均。故明人小楷,精而无逸韵。
唐隶之不可学,亦是太均。右军云:“平直相似,状如算子,上下方整,前后齐平,便不是书,但得点画耳。”故要在点画以外,自有气势体息。至唐人草书,不可为训,则以流于狂怪也。
唐人无不学右军。欧、虞、褚、薛四家,称各得圣人之一体,然颜柳二家,实自成一大宗派。至宋人学书,几又无人不学平原者。东坡云“书至于颜鲁公”,是极推重语。然其书黄子思诗集后云:“余尝论书,以为钟王之迹,萧散简远,妙在笔画之外。至唐颜柳,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,极书之变,天下翕然以为宗师,而钟王之法益微。”亦有微辞。米襄阳祖王而宗颜,于颜所得实夥。然其言“颜柳跳踢,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,从此古法荡然无遗矣”云云,其于恶习,亦可谓力诋矣!大概颜有俗气,柳有匠气,学者不可不知。
司空图论诗曰:“梅止于酸,盐止于咸,饮食不可无盐梅,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。”书法何尝不如此。譬如画止于平,竖止于直,同此笔画,同此几字,而李四张三,写成不同,王五赵六,亦复异趣。所系人各有性情胸襟,调味手亦自不侔耳。
学者有志于书,初步学楷,每苦不能入,渐欲灰心;略有得,又苦不能入,又欲灰心,此仅第一二阶段耳。过来人都能相视而笑,初非足患。递取一二月来所习,前后对比,自知之矣。“明道若昧,进道若退”,正此之谓。唯有一种人,无论何种碑帖,一学即肖,一肖便谓天下无难事。学既杂,离帖仍是自家体路,因复自弃。聪明自用,方是危险!
,或是经验。学者求师实际,止在老马识途一点。至于功力,是在求己。昔颜平原从张长史指授,长史但云“多练习,归自求之”而已。俗有妙语:“夜半摸得枕头何曾靠眼。”还不是与孟子说“自得之,则资之深。资之深,则取之左右逢源”同一机括。相传古人传授笔法,似乎极难,或且至之神话,无非要学者专诚之至。得之难则视之珍,庶几可成功也。
客去录
文字亦近四千,分十六章节。
前有自序:
“避地海上,倏焉十载,
卧云深若与世忘,
其间所往来者,
多艺文秀士,瀹茗著酒,
亦以忘忧,及门二三子,
每以所闻于予者,
窃为纪录,
意隔文疏,
或不成片段,
然嘉其用心之勤,
辄取以点正。
今附刊于此,
且使承学之士得闻诸论,
而贤者下问,
余亦得免于辞费焉。
题曰:‘客去录’。
复翁自识于云深处。”
本篇大多为议论古之谈,
今随挑数则以示观者。
赵松雪书,天资不足,功力甚深,其秀媚最悦俗眼。商贾笔札之美,求小成者趋之。
松雪功力,见于其楷。然千篇一律,万字一同,正董思翁抉其受病处在“守法不变”。世传《兰亭十三跋》、《天冠山诗》等,为其行书之最脍炙人口者,奈逸韵骨气,终不可强钟书点画。
余谓书法之功,尤贵乎力,惟其力乃如太极拳。外道以为全不用力,不知其中浑身是力,功夫在内。
稳非欲,险非怪,老非枯,润非肥。审得此意决非凡手。
书言八法,始自唐人;论书入于魔道亦自唐人,而宋承其风。然宋人已自非之。如黄鲁直云:“承学之人,用《兰亭》永字,以开字中眼目,能使学家拘忌,成一种俗气。”
包慎伯好为玄论,终身不懂笔法,观其议论与书法可知也。其“述书”中征论笔法,张三李四,王五赵六,七张八嘴,全无主意。其所闻道之各家,看来全似野狐禅;其自诩悟得处,亦属莫明其妙。
时下所谓“太史公”字,非书家,不足论,然卷子字着实下过工夫,亦偶可称善书者耳。
各异,右军万字不同。盖物情不齐,变化无穷,原为天理,岂盘旋笔札间,区区求象貌之合者乎!此学魏书者宜知,而松雪不知也。
“杀(杀)字甚安”一语,出晋书卫传。杀字作一字之结构布置讲。包安吴论书,每喜用之。于此颇忆一笑话,宋代沈括论书云:“凡字有两字三四字合为一字者,须字字可折;若笔画多寡相近者,须令大小均停。所谓笔画相近,如杀字乃四字合为一,当使木几又四者大小皆匀。”此必为读卫传不得其解,乃为穿凿之说,已甚可笑,至复论一未字云:“如未字乃二字合,当使土与小者大小长短皆均。”是不通小学,横将字体腰斩。天下第一笨伯,偏要做聪明人。想当时闻者,必有作掩口葫芦者矣。
书法之递变,全属时代自然之趋势。故篆不得不变为隶,隶不得不变为章草、今草及楷行。前人有“小篆兴而古意失,楷法备而古意离”之叹,是在求古之言则然。
隶分一路,近代推郑太夷,并世则钱瘦铁独美。瘦铁不以书名,而其隶分古拙劲健,一时无两,其余诸子几无一笔入汉。偶见梁庾元威讥时人书云:“浓头纤尾,断腰顿足,一八相似,十小不分。”正说着今人之病,为之失笑。
晚年的白蕉在华东医院养病期间(摄于1965年)
右军草书小真书,不必言矣。其楷之灵和,与大令草行之神骏,俱为绝诣。今人仍有拾包康一辈牙慧,以为帖俱是伪而不足学者,既自被欺,更欲欺人,正坐不学。
楷书与行草,魏晋人最高,而钟王为代表。学之者须天分、学力、识力并茂,而胸襟尤有关系。且学钟王字无从讨好而容易见病,因此急功者都不肯学,亦不敢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