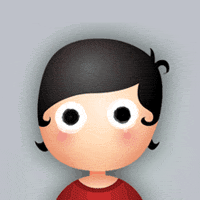世上许多道理,其实都跟吃肉差不多
一开始,你看见一盘酥烂挂酱的红烧肉,喷香扑鼻,你就想来碗白米饭,吃了它。
后来,你吃过许多红烧肉了,自己也做过了。你看见一盘红烧肉,就会下意识的考虑:这是五花肉还是肋排肉?这红色是炒的糖色还是老抽上的?八角分量如何?是不是下了桂皮?这肉煎过没有?是炖的还是蒸的?这盘肉在你眼里支离破碎,分成无数细碎点了。甚至你还会情不自禁的去分析:这地方产猪吗?如果不产猪,猪肉是哪来的呢?下厨的阿姨手脚干净么?用什么方式挂猪皮上的毛呢?……
最后,你叫一碗红烧肉,看到的就是红烧肉,酥烂挂酱,喷香扑鼻,你就想来碗白米饭,吃了它。
为什么你不会再情不自禁的考虑了呢?因为其一,你已经自信到了不必用这种方式来下意识的自我证明“我是懂红烧肉的”,你深知自己随时可以判断一盘红烧肉的好坏之后,就没有这心思了。其二,你确实也已经吃过了太多红烧肉,所以你会对世上红烧肉的诸多不如意处不加介怀,而去专心感受红烧肉那具有共性的美妙部分——肥厚重味,别的管他娘。
简单来说,最后之所以你看红烧肉还是红烧肉,一是你放过了世上的红烧肉,二是你放过了自己——当然,前提是,你确实懂了红烧肉,而且你知道自己懂了。
这就叫:见肉是肉;见肉不是肉;见肉还是肉。
这里的红烧肉,当然也可以替换成其他许多词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世上一切智慧,其实都可以归纳为:
对尚未被归纳为知识的或尚未被自己接受的东西,给出相对准确的判断。
换句话说:
知识是个圈。你知道得越多,圈的半径越大,你就知道了越多先前不在你知识圈内的东西。
所以知道越多,越觉得自己知道得不够,就这个道理。
而智慧则是另一回事:它使你有能力,去判断不在你知识圈内的东西。
有些人(非常少)天生有智慧;而更多人则是通过归纳、演绎和总结。
孔子说,学而不思则罔。学就是获取知识,思就是从知识里提取智慧。
孔子又最讲究举一反三。举一反三,不学而能归纳判断其大概,也就是智慧了。
因为到最后,能教授的一切,毕竟还是知识;而归纳推演、触类旁通,却只有自己能做到——老师没法帮你触类旁通,所以,智慧必须自己来。
我妈爱看菜谱,我爸从来不看;但我爸下厨很了得,我妈也服。他做鱼头汤,炖排骨汤,炖红烧肉,煮花生,做麻辣豆腐,都很好。我问他怎么会的,他说他处理食物,万变不离其宗:先用油或少油,把食材略煎一煎炒一炒,炒香了,加水煮炖;味道重的调料就先干炒出味,清淡些的调味料则到起锅前才下——这些经验,最初是他做鱼头汤做出来的;被他放之四海,试了各类食材,好像都还能用上。
我觉得我爸就很有智慧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肉类不一定是越新鲜越好吃。像欧洲17世纪就有这样的技术:肉牛养殖,是买六七个月的小牛回去饲养;养超过三十个月后,宰杀,不能立刻吃;肉剖开,经常还悬挂,这期间,最主要的目的是:
让肉类蛋白质,分解成氨基酸,一方面改变肉类的酸碱度,一方面增加肉的风味和口感,所以熟成十到十二天的牛肉,比刚宰的牛肉好吃些。
如果不拘泥于肉类,推而广之,许多食材都有类似的处理方式。只是相比肉类熟成,要多一些手续和添加料。其结果,就是等待起化学反应,使之味道更适于食用。
比如火腿,早期粗制法就是猪肉揉大粒子盐,配合悬挂风干;挂久了,就有猪肉和咸味之外的鲜味了。
比如鲣节(刨出来就是木鱼花),是新鲜鱼肉,经过各类手法——有的是直接烟熏,有的是等肉表面霉变之后所成。
比如各类腌蔬菜,大多都跑不过乳酸菌起反应。
比如东北一些地区晒大酱。
比如红茶。比如雪茄。比如奶酪。
年龄老的葡萄酒,倒进杯子里,如果等一等,等葡萄酒和空气氧化之后醒了酒,味道会好些。
但如果醒太久了,把一杯葡萄酒放个十天半个月,就没味了。
同样,肉也不能搁太久,不然就真腐败了。所以食材熟成,也需要熟练的老手来掌握尺度。比如老年间浙江的制火腿名家,拿筷子给火腿戳个洞,看看:好了,腌完了。
我认识一位东北朋友的外婆,耳朵凑缸边,敲敲,听听,就知道酱好了没有,“再不吃就臭了!”
这种做法当然有点浪费,绝大多数食材熟成或发酵后,重量会大幅度削减(主要是水分大量流失)。但味道却会变得更好。
就像你吃腌萝卜,肯定不如新鲜萝卜水分足重量够,但味道更好些。
写过东西的人都知道:真坐下去写,犹豫和斟酌的时间居多,敲键盘的时候少。人会不断给自己找理由:没找到节奏感啦,没灵感啦,不满意啦,如此云云。
而且灵感这东西,确实不易得;许多时候,写着写着,自己都恨:清汤寡水,什么破文章?!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有个法子,可以克服拖延症,如下:
每天,趁闲着发呆时,想你最想写的东西。想出一句话,最真实最简单的一句,或者一个最简单的意象,然后延伸,把它及其周遭的东西,组织得很美。
但不要急着写,就在肚里搁着,来回酝酿着,把这一段前前后后的都想圆润了,想得你觉得不吐出来不舒服的时候,就可以开始写了。
这一写,不能停手,就写到你高兴了为止,在最高兴的时候停下来,想好下面的一句话不写,留着。
这就像评书留个扣子,明天好写。
这就像,把句子当肉,搁着,等它发酵出鲜味来了,再吐口,一蹴而就。
当然不能搁久了,久了,句子就失去新鲜感了,腐坏了。哪怕你念给别人听,别人赞美“好句子”,你自己都要摇头:不好不好。你就失去这个句子了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有点上进心的人,都知道该看大部头书,但大部头书读起来困、烦而闷,为什么?信息量忒大,密度大,像牛肉干,啃着知道好味道,但腮帮子疼。
福楼拜早年喜欢雨果,后来不喜欢了,很大部分原因是,雨果老是大骨头棒子带大肉直接扔给你,不管你啃不啃得动——再厚重的骨头棒子也受不了啊。
所以,人会愿意看些没营养的文字,好比吃婴儿米粉。婴儿米粉当然不如大骨头棒子钙质足,但不用嚼,不费脑子,甜滋滋,好吃。
怎样算有肉味的文字呢?举俩例子。
一个例子,大家熟透了。王小波在《我的师承》里那俩对比。普希金的《青铜骑士》,查良铮先生的译本如下:
我爱你,彼得兴建的大城,
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,
涅瓦河的水流多么庄严,
大理石铺在它的两岸。
另一位先生译的《青铜骑士》:
我爱你彼得的营造
我爱你庄严的外貌
根据这个思路,再举一个例子。
段子一:
他阖了一会眼。他几乎睡着了,几乎做了一个梦。青苔的气味,干草的气味。风化的石头在他的身下酥裂,发出声音,且发出气味。小草的叶子窸窣弹了一下,蹦出了一个蚱蜢。从很远的地方飘来一根鸟毛,近了,更近了,终于为一根枸杞截住。他断定这是一根黑色的。一块卵石从山顶上滚下去,滚下去,滚下去,落进山下的深潭里。从极低的地方传来一声牛鸣。反刍的声音(牛的下巴磨动,淡红色的舌头),升上来,为一阵风卷走了。虫蛀着老楝树,一片叶子尝到了苦味,它打了一个寒噤。一个松球裂开了,寒气伸入了鳞瓣。鱼呀,活在多高的水里,你还是不睡?再见,青苔的阴湿;再见,干草的松软;再见,你硌在胛骨下抵出一块酸的石头。老和尚敲磐。现在,旅行人要睡了,放松他的眉头,散开嘴边的纹,解开脸上的结,让肩膊平摊,腿脚舒展。
段子二:
茶干是连万顺特制的一种豆腐干。豆腐出净渣,装在一个一个小蒲包里,包口扎紧,入锅,码好,投料,加上好抽油,上面用石头压实,文火煨煮。要煮很长时间。煮得了,再一块一块从麻包里倒出来。这种茶干是圆形的,周围较厚,中间较薄,周身有蒲包压出来的细纹,每一块当中还带着三个字:“连万顺”,——在扎包时每一包里都放进一个小小的长方形的木牌,木牌上刻着字,木牌压在豆腐干上,字就出来了。这种茶干外皮是深紫黑色的,掰开了,里面是浅褐色的。很结实,嚼起来很有咬劲,越嚼越香,是佐茶的妙品,所以叫做“茶干”。连老大监制茶干,是很认真的。每一道工序都不许马虎。连万顺茶干的牌子闯出来了。车站、码头、茶馆、酒店都有卖的。后来竟有人专门买了到外地送人的。双黄鸭蛋、醉蟹、董糖、连万顺的茶干,凑成四色礼品,馈赠亲友,极为相宜。
两组文字,是同一人写的。汪曾祺先生。第一段才气纵横,锋锐无当,是他二十四岁时写的;第二段温厚含蓄、沉静自持,是他六十五岁的作品。
这里当然没法比文字好坏,因为风格各异;只针对最普通的读者,他会觉得哪段文字更有肉味呢?
汪曾祺先生在《小说笔谈》里,给自己的语言观、节奏观、结构观,写了许多,但如果往他文字里找,其实很容易:不要着急。
密集的内容当然比淡而无味好,但倾吐内容的方式,就是风格和文体。急切的倾吐出来,味道凶烈,但可能让人啃不动,比如译文作品,许多都保留着长句结构,就难啃,肉太紧啦;慢慢来,有筋有节,有软有硬,就有肉味了。五花肉所以好吃,就因为肥瘦肥瘦肥瘦,松的紧的,长的短的,相间着。
文章也是。